陳野叉著腰杵在倉庫門口,鼻孔里鉆進一股潮濕發霉的怪味。他祖**那輩兒蓋的紅磚墻被歲月啃出蛛網般裂紋,銹跡斑斑的鐵門上還沾著上個月防汛時濺上的泥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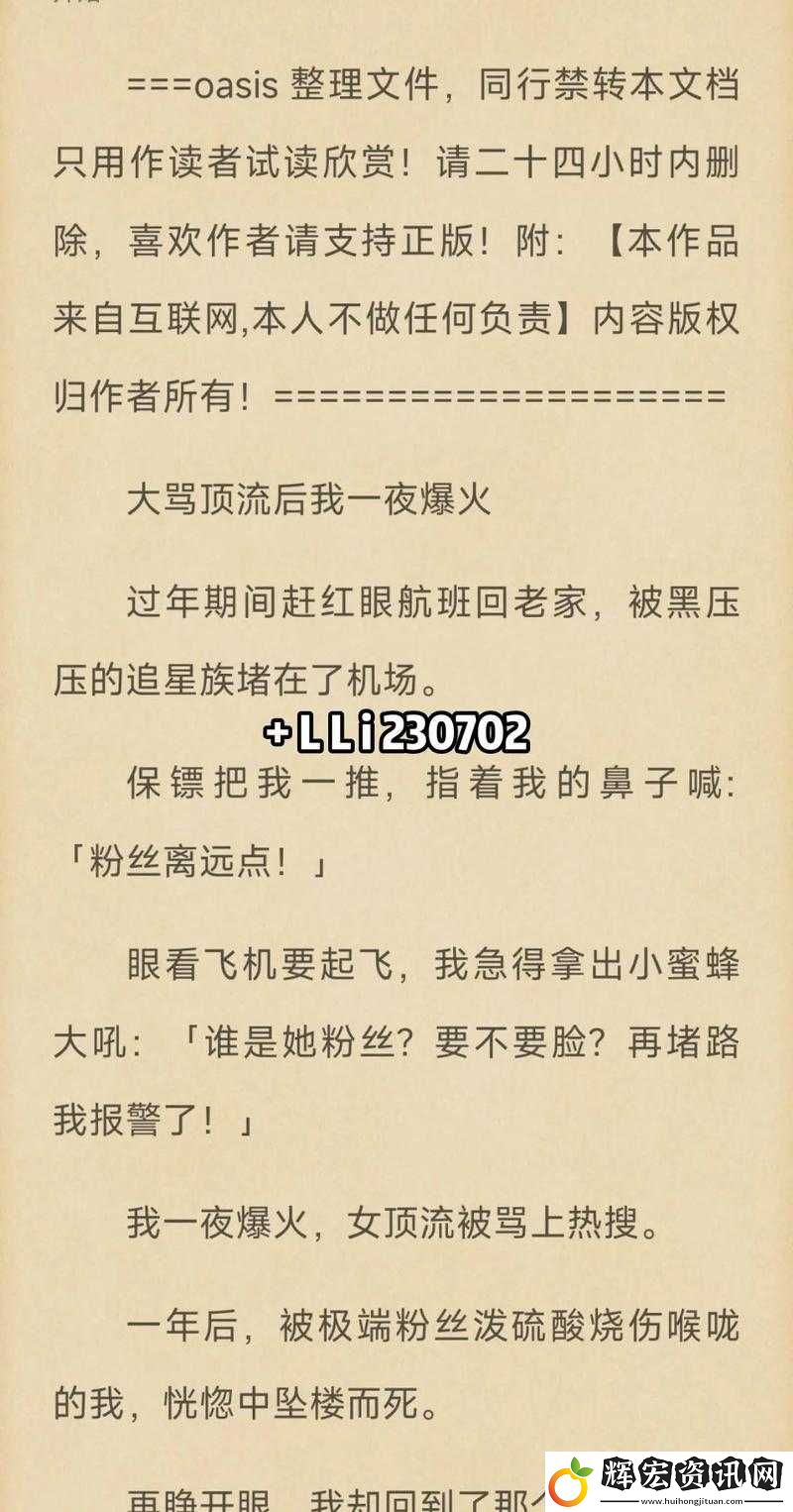
"我說不許進就不許進!"他朝攥著鏨子的瘦小男孩吼,唾沫星子差點迸進對方耳朵。這小子穿著沾著草籽的灰布衫,肩胛骨上馱著個布包,布包里沉甸甸地硌著半個腦袋。
"我要見倉管!"瘦男孩犟得像頭撞了南墻的驢,"我姐讓我帶著信,等不到明兒天亮就要見倉管!"
二、她拖著傷來找他
陳野把鐵鎖從褲腰里掏出來,拇指摩挲著鎖孔邊緣的豁口——這毛病要從五年前那個雷雨天說起。那會兒他奶奶剛走,他蹲在倉庫后墻角抽旱煙,突然炸了個雷,把排在倉頂的瓦片震得七零八落。
"救救她!"有人把半截衣袖絞成一團往他鼻尖戳,暗紅的血水浸透了麻線。是村口張屠戶的小女兒,后背上插著把淬過毒的柳葉刀。陳野蹲下去摸脈搏時,袖口那截燒紅的鋼筋正要壓進貯存稻谷的麻袋堆里。
三、月光下的那場談
三更天,曬谷場上的青石板還淌著露水。陳野卷著旱煙葉子蹲在石階根子上,身后傳來踢踢踏踏的拖鞋聲。那是個一瘸一拐的影子,布衫子的左袖管空蕩蕩地飄在風里。
"大晚上跑什么喪?"他把旱煙鍋子往石板上夯,火星子迸進草窠里。
對方轉過臉來的瞬間,陳野愣住了——是白天那個瘦小子換上女裝的模樣。脂粉涂得比灶王爺年畫還濃,嘴角的疔瘡把口紅洇出一圈烏青,但那雙眼睛亮得能戳瞎人。
四、雨夜里的那碗藥
第二天天剛亮,陳野就被人搡進老支書的竹椅間。吱呀呀一張老式鐵床頂在墻角,被面上繡著已經褪色的富貴長壽圖。床上躺著個顴骨很高的女人,眼角刀疤往下耷拉著,嘴角吊著半吊銅鈴鐺。
"聽我說完,你再摔門出去。"那人摘了鈴鐺湊近床頭柜,瓶子里裝著黑黢黢的藥膏,和陳野前年治燙傷的單方有三味藥引子生熟顛倒。
五、八月十八的那場婚
曬谷場支起紅綢緞帳子那天,陳野把倉管鐵鑰匙別進褲腰帶。他祖**臨終前攥著這串鑰匙沒松手,后來隊里的人刨開他枕下的糯米團子才掏出來。今兒個要娶進來的娘子,左胯上紋著條火紅的蜈蚣,指甲縫里還沁著沒擦凈的朱砂。
夜深了,倉庫里傳來咔嚓咔嚓的機械聲。這次是真的要拆老墻了,磚塊落地時揚起的塵土里,陳野看見飄著幾片泛黃的賬本殘頁。他想起三天前,那個戴鈴鐺的啞巴支使手下人時,手上牽著根看不見的細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